之前在微博上提过一嘴,因为文字量比较少,所以也没想往博客上放。昨天小读书会中又提到了这个问题,想想还是贴一下,毕竟是一个对哲学的基本定位问题。
拜占庭人应以罗马自居
师承吴老师,我的哲学立场当然是偏向于欧陆现象学的,不过其实我不太愿意以现象学或欧陆哲学自居。就好比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外人叫东罗马、西罗马,后来又管东罗马帝国叫拜占庭,但其实拜占庭人并不以拜占庭这一旗号作为自我认同,而仍然是以“罗马人”自居的。哲学也是类似,20世纪哲学分裂为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欧陆哲学又被称作现象学,但这是外人眼里的界定,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是“欧陆哲学家”,也不是“现象学哲学家”,我们就是“哲学家”。我们的祖师爷并不是胡塞尔,而是柏拉图。
当然,这么一说就有点不吉利了,拜占庭帝国虽然号称继承罗马正统,但总归是日薄西山,逐渐萎缩,最后只剩一座孤城苟延残喘,反而是“蛮族”的后裔日渐壮大。现象学似乎也是类似的命运,它已经逐渐凋零了。
我们偏向现象学的人,可不能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正视现象学传统已日渐萎缩的现状。当然,局外人会认为,是英美分析哲学取代了/压倒了现象学的位置,而对我们来说,我们面临的其实就是“哲学”本身的萎缩。
现象学的策源地,德国,其哲学界也早就英美化了。现在也只有法国还有相对较浓的欧陆哲学色彩。但既便如此,我们也要看到,现象学的衰微是不可阻拦的时代大势。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一种绝望和悲观的态度。相反,认清自己的命运才能够认清自己的使命,才有可能积极地有所作为。
科学崛起下的哲学分裂
为什么现象学传统,或者说古老的哲学传统本身,在这个时代必然会趋于衰落呢?
这要分两个阶段来讲。第一阶段是从古典哲学的最后辉煌——德国观念论之后到20世纪初,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科学”的兴起。一方面许多古老的哲学话题被科学家们接过去了;一方面哲学也开始了“专业化”。康德可以说是第一个以“哲学教授”为谋生职业的大哲学家。康德以降,哲学家们栖身于大学院校之内,与其它“专业”相并列。
哲学作为“爱智慧”,现在变成了“智慧之一”,从求知的基础,逐渐变成了一门专业知识。与之相伴随的是“分科之学”的崛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羽翼丰满,掌握了对“知识”乃至“真理”的话语权。
双重意义上的“科学”(分科化和对自然知识的垄断)对哲学步步紧逼,而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分野,就发生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一部分人认为,哲学应该向科学俯首称臣,应当像当年科学之于神学那样,做现代科学的“婢女”,哲学家的唯一使命,就是“帮助科学家澄清概念”。这就是分析哲学的缘起。虽然这一帮助科学家澄清概念的任务,他们也未见得完成得多好,但是毕竟还是在现代科学的分科体系下保留了一席之地。在建制得以保证的情况下,当代的分析哲学家的姿态倒也不见得那么低下,但是最基本的定位并没有改变,即无条件地臣服于现代科学——包括其结论,更包括其方法和态度。
欧陆哲学走的是另一条路,或者说另几条路,总之并不轻易向科学投降。包括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路径,揭示“欧洲科学的危机”,试图为科学重新奠基。在这方面,诸如法兰克福学派之类对伴随现代科学兴起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也是另一条路数。还有诸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又诸如西班牙哲学、东正教哲学等偏向灵性的另类路数等等。总之,除了向科学俯首臣称之外,欧陆哲学代表着另一种态度,或者说哲学家原本的态度,亦即超然、独立的立场。
需要注意的是,超然于科学并不意味着要去凌驾于科学,乃至要去指挥科学。就好比古代哲学家的立场当然会超然于工匠之上,但他们并不会去指导工匠,也并不认为工匠的技艺是错误的或不牢靠的。古代哲学家心安理得地居住在工匠建筑的楼房中谈天说地,而现代哲学家也当然可以安居在现代科学所塑造的世界中高谈阔论。
现象学承认现代科学的诸种成就,就好比古代哲学家接纳工匠创制的诸种器具那样——它们固然是有效的、是可靠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但还并不是爱智者所爱的东西。
历史性衰落:偶然的与必然的
第一阶段的衰落对现象学和对分析哲学而言差不太多,分析哲学家们尽管主动投靠科学,但科学家们爱答不理的,并不是很买账。最后也只是在现代学术体系的边缘之处勉强依附罢了。相反,欧陆哲学家倒是一度名家辈出。
然而,在下一阶段,欧陆哲学显然受到更大的阻力,乃至于一蹶不振了。
为何如此呢?一方面,有一个相对偶然的,但也非常致命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崛起及其相伴而来的英语在全球学界的称霸地位。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厚重的哲学传统,在本土兴起的实用主义哲学,虽然也算深刻,但也从侧面暗示出美国人的务实氛围。再加上,英语也是相对最直白、最对象化的语言之一。因此英美的文化氛围和讲求清晰明了的分析哲学最为般配。随着美国的崛起,让这种未必最为优美的语言成为世界语言,那么与之最贴合的分析哲学也自然就独领风骚了。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恰恰是法国哲学能够保留最多的欧陆哲学风格,这显然与法国人对法语的独特情结有关。
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隐晦,但无可逃避的因素扼制了欧陆哲学的发展,那就是学术界“媒介环境”的变化。
传统上说,哲学家的作品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著作”。我们读古代哲学家,都是以一部又一部“砖头”一样的经典著作为单位去阅读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部一部啃完才是哲学入门的方式。读哲学,就是读哲学著作,这在传统上看是理所当然的。
除了著作之外,那就是口头的讲授了。传统的学术制度也是以“讲席”为主要单位的,但并不是以现在那种学术会议上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快餐式报告为主,而是以长篇的系列讲座,或者一学期一学期的讲课为主要形式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很多著作,也都是讲义的结集。
然而在当代,主流的学术作品并不是著作,而是“论文”,一篇论文只有几千字,甚至很多人需要在不到500字的摘要中就看清楚你的结论。
要注意,把十几篇论文攒在一起,并不能形成一部著作。或者说,一部哲学著作,不可能拆分成十几篇论文。试想一下,你要怎么把《纯粹理性批判》或《存在与时间》拆成论文发表呢?
当然,倒不是说欧陆哲学家就不会写小文章,或者英美哲学家就不会写大部头,但是关键在于,欧陆哲学的内在特点,决定了他不擅长写小篇的论文。那么,在以论文发表为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以论文和会议报告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方式的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之下,欧陆哲学自然是要衰落的了。
哲学家为什么不擅长论文
分析哲学更擅长以论文为单位发表作品,恰恰和他们依附于“科学”有关。对科学的臣服未必能给科学家提供多大帮助,但至少能给他们自己提供一个关键的帮助,那就是更容易地建立公共的共识平台。首先,自然科学的主流结论和一般方法,就形成了分析哲学家们展开讨论时的一个天然的公共基础。其次,遵循分科之学的逻辑,分析哲学家擅长把一个的论域条分缕析,把问题拆分、析出,最后聚焦到一个小部分去进行讨论。问题拆得越细,大家讨论得就能越有针对性。
然而,前面讲到,现象学家并不顺服于科学,而是以各种方式要为科学重新奠基,所以往往是分析哲学家刚开始拆分第一步,现象学家可能就不同意了,因为任何问题的关键恰恰都在于其“前提”——我们究竟是如何可能理解这一问题的?这一拆分究竟何以可能?这些问题都不能轻易放过。
因此,现象学家和所有传统的哲学家一样,很难找到一个公共的基础平台,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以自己的思路追根溯源,并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搭建自己的理论大厦。那些体系型哲学家当然要建立一个自圆其说的宏伟大厦,而那些“反体系”的哲学家呢,就更不愿意轻易认同一个现成既定的公共知识体系了。所以,他们总是自说自话,而很难加入一个高度细化的公共论域之内。要理解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显然,一篇几千字的论文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从最终在学术界沉淀下来的作品来看,英美哲学往往是以“命题”为单位的,比如“休谟问题”、“罗素悖论”、“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塔斯基的真理定义”、“蒯因—迪昂论题”、“古德曼的新归纳之谜”、“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查尔默斯的难问题”……一位位分析哲学家的贡献,以这样一个一个命题的式样沉淀到学者们的共识平台。甚至分析哲学家更是用这种方式去解读古代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条分缕析,分拆出一个个清晰明确的命题或主张。比如康德一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分析哲学家就读出一句“存在不是谓词”的命题来,就津津乐道,仿佛给了康德莫大荣誉。
这不是传统哲学的风格,这是现代科学的风格。现代科学家只需要知道牛顿三定律,而并不需要去整本阅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过往科学家的贡献,可以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记录在最新的教科书中,而伟人的荣誉无非是变成了一个个命题或符号的“冠名”,但除了名字和命题之外,大部头著作和整体的人格都退隐了。
相反,现象学家的风格更接近于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他们为世人留下的是一部部著作。海德格尔的贡献,就是《存在与时间》,或者说“海德格尔哲学”,而不是什么“此在定义”或“座架猜想”。胡塞尔的贡献就是“胡塞尔”,康德的贡献就是“康德”。两千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在读《理想国》,一整本地读。
现代人习惯于科学化的思维方式,习惯于基于现成的、公共的概念基础去阅读任何人的作品,而不愿意沉下心来慢慢进入每一个哲学家独特的思想空间,于是自然就会对哲学家的传统风格嗤之以鼻。比如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开头就引了一段黑格尔的话,加以嘲笑:瞧瞧这写的是什么东西,简直不说人话!
他们把哲学家肢解为一个个命题和一小段一小段言论的集合,拆分出一个碎片来鞭笞,当然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真正的哲学作品是人本身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分析哲学的,或者说现代科学的研究风格,是更适合信息时代的学术交流环境的,是更容易高产也更容易累积式进步的。
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投降呢?为什么还要抱着陈旧的风格不放呢?道理很简单,我们追求的东西不在这里。
就好比说,我们要找钥匙,那么是该去明亮的路灯底下找呢,还是去晦暗的密林深处找呢?路灯底下清晰明确,而且很容易划分区域,分工合作,你搜这个街区,我找那个街区,效率极高,时不时还能收获几个硬币。而在密林深处,晦暗无光,边界模糊,甚至找不到同伴与你合作……所以说聪明人自然该去路灯下找喽?不对啊!该去哪里寻找,从来都不取决于哪里更明晰,关键问题是,你要找的东西丢在哪儿了?
那么做哲学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古希腊的箴言,无非是“认识你自己”;按照康德的说法,哲学追问的无非是三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或者一个总的问题:“人是什么”;按照最通俗的讲法,无非是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总之,哲学追问的是“我”,是“自己”。哲学从“我”出发,以“我”为归宿。哲学关注的,始终是不可替代的自我,没有人能代替我生活,也没有人能代替我去死。科学或工具可以帮助我做很多事情,但是要如何把它们认同为“我”的一部分并且像反思自我那样追溯其来龙去脉,却仍然不是别人能代替我做好的。
而“我”是完整的统一体,并不是由一片一片命题组成的,无论我从什么角度去追问自我的来龙去脉,“我”的个性都会贯穿于我的哲学之内。
当然,每一个我都不是超然世间的,自我与他人是可以交流的,但这种交流并不是“交换”。“我”并不像一个机器人或者一套乐高积木那样,可以拆出一些零件来直接拼接到他人身上。人的互相理解,是通过“同情”,通过“同理心”来达成的。
哲学家真正关切的,始终是他自己,是他的“我”。因此,哲学家真正的作品,也恰好就是他自己。哲学家通过著作,把他所反思和追寻的“我”呈现出来、表达出来。
这是哲学家和诡辩家的根本区别——诡辩家发言和写作,是可以顺从于外在目的的,比如他明明不认同的东西,为了营造节目效果,或者为了忽悠骗钱,他可以从功利效用的考虑去谈论。因此诡辩家的著作未必有统一性。可以把他们的言论根据相关功用或目的分拆开来单独理解。但哲学家的写作是为了说服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因此,哲学家未必要费心搭建体系,他们的著述也总是会趋于统一,因为他们的著述无非是“自我”的表达,人格的统一性和著作的统一性互相确保,人格的独立性和著作的独立性互相支撑。
独立人格的形成,并不是在一个离群索居的抽象岛屿中可以完成的,独立人格的成熟要求交往,人总是在与其他独立人格之间互相交流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眼中没有其他的独立个人,而只有来自外界的无数孤立的“行为”,那么他的人格恐怕是不能健全的。
一个普通人,要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就需要把他人当作完整的独立个体去打交道。而一个哲学家,要在历史性的处境下反思和定位自我,也需要把其它独立的人格作为参照。
阅读哲学著作,不是为了从中摘取出有效用的只言片语,而是为了与其他自由而不朽的心灵打交道。
真正的哲学作品既不是论文,也不是著作,而是每一个哲学家自己。哲学家通过统一的、自洽的著述,把他们对自我及其处境的反思呈现出来。哲学家努力让自己作为完整的个性,而不只是苍白的冠名符号,在世间不朽。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媒介或技术环境如何演化,人类对自我的关切总是不息的,追寻不朽乃是一种不朽的追寻。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能反思的人,每一个试图在各种外在行为中体现自我的统一性的人,都是“哲学家”。区别在于,一般的独立个性,只是在与家人朋友的交往中彰显自己的力量,而那些成为经典的哲学家则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与遥远未来的读者继续交流。
有鉴于此,哲学固然会衰落,却不必担心它走向灭亡。除非哪一天人类不再关心自我之“一”性了,哪一天自我意识也可以像乐高积木那样标准化拆分重组了,哲学才会真正面临灭亡的危机。也许计算机不需要哲学了,人工智能不在乎“一”,一个智能程序可以随时分裂为无数同等的子程序再随时统合起来。对于这样的智慧体来说,古老的哲学传统恐怕真的过时了。但至少对今天的人类而言,“命题哲学”还远远不能取代“个性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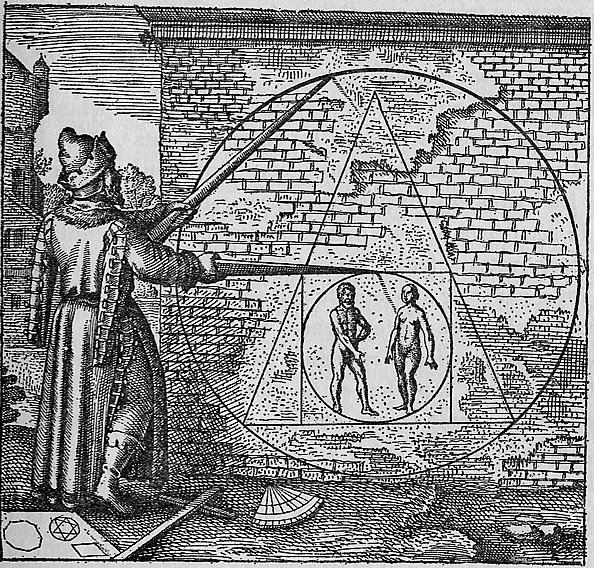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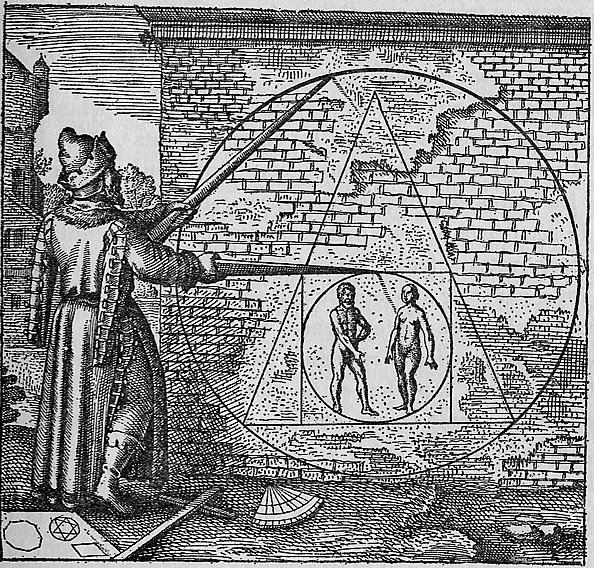
老师,读了您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科学的崛起导致20世纪哲学的分裂,以德国为代表的现象学和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作为科学依附的分析哲学还是以胡塞尔为代表个性哲学都有一个逐渐衰落的趋势。他们虽然各有优势但都在科学的大背景下颜色在渐渐消褪,从您的论点来看,您是倾向于欧陆哲学在哲学中的意义更加重大的一面。有没有一种可能,使英美的命题哲学与欧陆的个性哲学相结合,取其在科学发展中有能给科学加以利用的部分,同时保持自己对自我认识的探求,如果能满足这样一种诉求,欧陆哲学不仅不会衰落,还会重新被人们注意到?
英美哲学有什么可被科学加以利用的部分吗?可悲的就是这一点,哲学家想给科学打工,科学家也嫌弃啊。比如费曼就说科学哲学之于科学就好比鸟类学之于鸟一样没用。
如果说现象学想要“结合”,为什么不直接结合科学本身,而要去找分析哲学中未必被科学家认可的成分呢?现象学家确实应该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了解当代科学史,比如胡塞尔本身是个数学家,海德格尔了解海森堡的工作,梅洛庞蒂自如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案例,这就是哲学与科学的结合,但不要指望科学家来用哲学,分析哲学也没做到,现象学更没必要去做。
哲学家不能忽视科学。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宰,想要反思自我,就必须要直面科学,要去学习和理解科学及其力量。所以哲学家要去结合科学,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为什么科技史与科技哲学是当代哲学家的必修课。但哲学并没有必要去满足所谓被科学利用的诉求,哲学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工具。
衰落是必然的,任何对“不会衰落”的奢望都是头脑不清或定位不明。但哲学永远不可能不再被人注意到,总有人注意得到,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罢了。
老师您好,请问按今天中国目前的学术现状,是否可以认为现象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在中国学界焕发当今欧陆学界所不具有的新的生机呢?中国是否有可能成为未来欧陆哲学的策源地呢?
中国本来就和现象学思想比较亲和,海德格尔也认为中文是一种美妙的语言。但现在中国学界的现象学繁荣未必是好事,很多人是把现象学当作可以反复咀嚼的文本对象,或者卖弄起来就天花乱坠的术语库。许多现象学研究者实质上是“现象学文献学”研究者,或现象学黑话专家,与传统哲学的旨趣相去甚远。
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不需要去策源什么欧陆哲学,我们该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接过手来,融入中国风格,发扬光大。
读完这篇文章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以后有人问我“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区别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现象学?”这类的问题,我就直接把这篇文章发给他看。
学生的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感触就是,在国内学界的大环境下,分析哲学一家独大的局面恐怕很难改变。一方面高校特别强调量化考核,分析哲学方向的确实比较发文章,效率极高(这点比较有趣,我问过几个分析方向的同学,他们并不赞同,反而认为分析哲学的文章技术含量较高,论证严密,门槛较高。而现象学的文章很多都是模棱两可、玄之又玄的东西,似乎比较好写)。另一方面高校特别强调国际化(其实就是以美国为尊)。看到英美目前分析哲学是显学,就都向这看齐。而且,不光是学校层面,在哲学系学生里面,我就认识好几个从现象学转到分析哲学方向的学生。原因不外乎几个:现象学对哲学史要求太高,强调精读大部头原著,而分析哲学以读论文为主;现象学基本都鼓励学德语法语,而分析哲学只用英语就够了;分析哲学上手快,专业细分,学个几年就很容易成为某个问题的专家,获得感比较强,而现象学很多人学了硕士三年,觉得还是一头雾水,很难说自己懂了海德格尔或胡塞尔。总而言之,就是学生们会觉得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如果说欧陆传统培养的是哲学家,那么分析传统培养的是哲学专家。就大多数同学来说,可能后一个身份更有操作性,也更有吸引力。
有时候我们也相互调侃,以后国内哲学各个二级学科下面(除了中哲),最能保持欧陆哲学传统的得是马哲了,因为学科特性,马哲是最不能被分析哲学渗透的学科了。所以,以后搞欧陆哲学的人得向马哲靠拢。当然,这些都是我们这些酸学生的玩笑话。
在中国很多期刊上真的是搞点玄之又玄的黑话更容易发表,但随着近年来期刊水平提升,越来越与国际接轨,现象学在国内也同样不那么吃香了。这种衰落并不可悲,“黑话现象学”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从这个思路看,其实欧陆哲学并不真的面临衰落,而只是在印刷文化主导的现行学术体制内受挫罢了。现象学作为向希腊本源的回归,在我们这个越来越重新具有口语文化特征的时代,或许恰逢其时。那种在会饮和散步中当场发生的、非对象化的哲学探究,说不定会乘着某种新生媒介的浪潮,以新的面目归来。或许有一天,我们不是阅读柏拉图自己也瞧不起的文本,而是走进VR阿卡德米,与苏格拉底AI交谈。
回到柏拉图,“哲学”不是任何成文的学问,而是一门灵魂自我升华的辅助课程。印刷文化把知识外在化、对象化了,但这种外在化达到极致时,例如人工智能的时代,外在知识干脆变得异己化了。因此在新时代,作为“灵魂修炼/内在统一性建构”的“哲学之路”或许真能复兴吧。
在追求哲学的路上不忘初心。
技术时代,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的技术的盛行同时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终结。然而,作为思想的哲学是否终结?在作为思想的哲学中是否还留有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思想的可能?倘若有的话,表达这种可能的思想的语言一定与适应于技术时代的信息媒介迥然相异,它对越适应技术时代的人越“不可见”,即使见到了,也只会视而不见。我想,这种可能的思想的风格应当是谦抑而坚韧的,表达这种可能的思想的语言应当是质朴而少言的。这种可能的思想很可能无法也无需产生多么强大的效能以至于被多半讲求效益的人类普遍接受。它只向需要它并以虔诚的态度期备它的人赐予自身。
胡老师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思想新鲜和观点独特。
1.欧陆哲学的衰落蕴含在哲学整体的时代困境里:分科之学的兴起与自然知识的垄断。
2.欧陆哲学的衰落和语言的关联。英语的简单和工具性使其迅速普遍化为学术交流的语言;反之拉丁血统的法语国家对自身哲学的捍卫
3.胡老师的媒介环境视角。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以单一的命题为思想单位,其学术评价标准也以论文为形式,由此很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线性积累模式;欧陆哲学注重思想体系的连贯性和人格精神的统一性,由此也就很难俯身参与公共话语的游戏之中(学术搞得好不一定论文发得多)。
4.个性哲学与命题哲学。哲学的问题答案不在公共话语的光亮显明之处,而在深沉的夜晚和幽暗的林地,在我身上。返回实事本身是要返回意识或存在本身;语言的澄清是一把重复削剪的剃刀。
与胡老师的不一致和没有被覆盖的地方:
1.对现象学与分析哲学截然二分的立场问题。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一书里将分析此传统推移到德语国家,胡塞尔和弗雷格关于意义与指称的一致性引人注目;分析哲学的开源者波尔查诺和现象学创立者胡塞尔的深刻关联。融合对话的意义更有价值。
2.科学重心的转移与哲学重心的转移:1纳粹的掌权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分子移民带来了一种政治上的学术后果,卡尔纳普,卡西尔等人离开德国。
3.欧陆哲学自身及英美分析哲学对其的影响:德国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反对黑格尔哲学的浪潮;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教条。
3.法国哲学有一种概念制造的盛相,这不能代替德国哲学思想的原创性。但上述观点肯定不能替德国哲学的没落辩护。
4.思想的语言与英语交流的语言。英语的直白和对象化是其作为交流的语言,法德语的性格位的变化更适和思想的表达。二者之间的不对称转而损害到思想本身。
5.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算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现象学年鉴》上,但这只是顺笔带下,不构成反驳。
就像佛教当初传入中国的情状,相比于德国,现象学其实是在中国。除了科技哲学,不知胡老师如何思考现象学和技术史(科学史和现象学的关联由于克莱因的努力已经成了有意义的研究)。技术史,科学史和现象学在中国可以都算得上是生嫩鲜活了。
刚注意到这里漏了一条评论没回复…应该是当时看漏了…还是感谢留言,说得都不错。不一致的地方我挨个回应一下。
1.从起源处当然能找到许多共同语言,但按照我的思路,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根本分歧并不是某几个个人的思想分歧,而是源于科学方法的风格路数分歧,个人的思想分歧当然可以摆在一起对比和对话,但个人思想更具偶然性,打通了某人与某人之间的思想关联,对于理解后世的思想并没有多大的益处。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共同语言不如说到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里找。
2.这一条被我归入第一个“相对偶然的,但也非常致命的因素”,即美国崛起的因素里了。
3.同意。感觉法国哲学有些过于浮夸,但总体而言也还是值得尊重。
4.这一条也被我归入第一个因素。
5.现在也还有类似著作的“博士论文”,不过学界还是以短篇论文为主了
最后,一种现象学的技术史,我从斯蒂格勒那里吸收了基本思想,即在我博士论文《媒介史强纲领》中讨论的“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媒介史换成技术史是一样的。另外,要把技术史作为现象学来研究,首先要把技术史作为思想史来看待,这方面我从芒福德那里获得基础,最近的领读与此有关,我会尽快形成论文。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k4y1276t?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