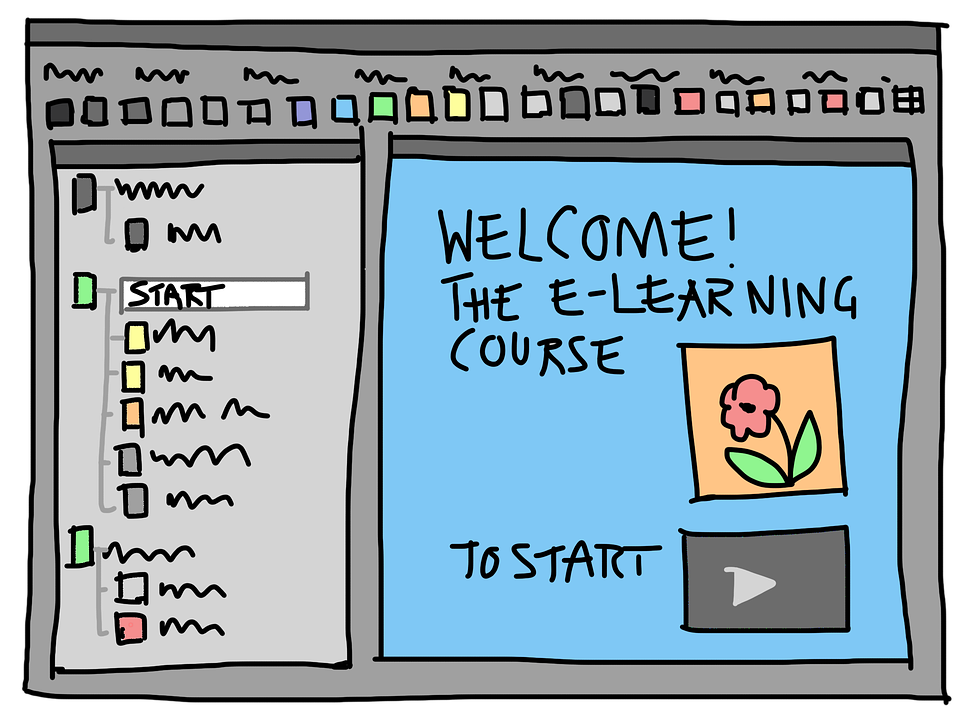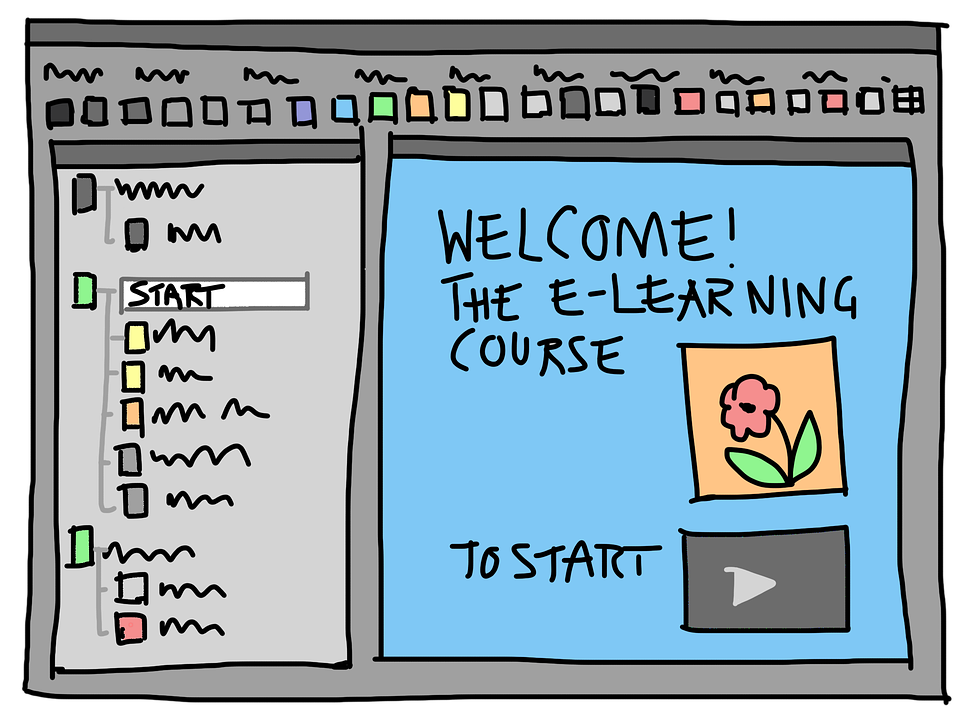又发在了界面上,转载请与界面联系~
发表时改得有点标题党,题目变成了“一块屏幕很难改变教育的命运,弹幕或许可以”,其实这句话不太准确,我的意思是教育的命运可能有多种改变方式,这块屏幕未必是好的方向。但大众传媒嘛,标题党一点儿我也愿意接受,内容方面没有大改。
发表时我把中间一段“远程教育的技术史”删掉了,其实删掉更通畅一些,但我这里还是贴上原文,这部分的主题可以在技术史研究上进一步挖掘。
是直播班还是尖子班?
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了“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起了广泛转发和评论,报道提到,3年来,贫困地区的200多所学校的7.2万名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全程跟随成都七中的教学,最后有88人考上清华北大。
对于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但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和转发者们,似乎想要表达某种更高的期待——新技术能够促进教育平等。文中提到“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十多年以后,似乎终于有了一点拿得出手成就了。
但是,这成就究竟有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远程教育的应用,是非常可疑的。事实上,文章中也写到为了配合直播教育,当地学校、教师和学生所做的无数努力,比如“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而这些努力,或许更多地应归功于当地教育系统的重视与督促,即便没有视频直播,如果贫困地区的教育系统能始终如此严格要求,如果各个学校都“紧凑”起来,难道高考成绩不会提高吗?
看报道,似乎并没有设置对照组来进行比较,甚至我们不清楚,被选择来开直播班的学校和学生是否原本就属于较好的一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把最拔尖的学生和最优秀的老师集中在一起,搞“尖子班”,这就是一种古老且有效的教学方式。尖子班无疑能够显著提升尖子生的成绩,但问题是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这种形式并不被鼓励,甚至是成为禁忌。但如果说这些“直播班”的组织形式首先就是一种“尖子班”,那么这种班级的成绩更高,未必能证明远程教育的意义,相反,可能更加剧了我们对教育公平的忧虑。
另外,把上清华北大作为教育的成果来张扬,本身就颇为可疑。首先,这是极少数尖子生的事情,并不能反映一般的教育水平;其次,清华北大的录取名额并不会随着远程教育的推广而扩容,远程教育也许能让一部分贫困地区比另一部分贫困地区更具优势,但未必会让所有贫困地区增加多少名额;我们看到,在接受同样的课堂内容后,贫困地区的200多所大学考上清北加起来也才能和大城市里的一所顶尖中学相比较,即便远程教育推广到全部贫困地区,也还是改变不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巨大鸿沟。
远程教育的技术史
让我们从这一“喜讯”中冷静下来,重新思考远程教育的问题。我们很快注意到,“这块屏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块屏幕的特点无非是把一个课堂的影像在另一个课堂播出,相关的技术手段只要有电视,早就可以实现了,根本要不了任何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甚至在许多方面,邮政时代的“函授”形式也可以完成,比如被直播班上某个理科状元津津乐道的事情:“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问题是,获取优秀试卷这种事情,几百年前的邮政系统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是件难得的事情?
“远程教育”这一概念随着互联网慕课(MOOC)的兴起再度掀起一波热潮,但它真不是什么新东西。那么几十年来,乃至上百年来,在“远程教育”领域人们难道不已经有了许多实践了吗?如果从优秀的学校“传来试卷”这件事情确实很好,那么难道它不该早就成为司空见惯的定例了吗?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仍然对远程教育的未来充满期待,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让人乐观——因为如果远程教育真能显著促进教育平等的话,那么它理应在电视时代乃至更早就展现了这方面的价值,而不是在今天轮到我们还要感到新奇了。因此,现在我们与其充满乐观地眺望未来,倒不如回过头来看看远程教育的技术史。
书面文字可能是第一项“远程教育”技术,它改变了知识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言传身教的境况,而让知识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进行传播。印刷术加强了文字的力量,批量印刷的教科书让文本成为教学的中心,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模式。
这些教育技术的应用,从结果来看,的确都促进了平等。例如文字的流行打破了口传文化中萨满、德鲁伊之类的祭司阶层对知识的垄断,而印刷术进一步打破了贵族的特权,让每个平民都有机会自学成才。
但深入历史细节,我们将发现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书写瓦解了原始的萨满教,但同时又促进了等级更森严的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印刷术让知识更廉价的同时,也强化了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圣经》的刊印促进了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女巫的铁锤》等印刷手册推动了残酷的女巫审判——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虽然发起于中世纪,但其真正流行全球却要借助印刷术的东风。
一项新技术在允诺一个美好未来的同时,也往往会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简单地拥抱新技术未必总会迎来进步,相反,新技术也可能令沉疴再犯,让某些陈旧的弊病借机膨胀。
在线教育的两条进路
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亲身参与在线教育的技术实践,他提示出在线教育有两条矛盾的进路:“工厂”与“城市”。
因为互联网技术本身就蕴含着两种力量,一是“自动化”,二是“互联”,这两种力量在教育实践中的不同侧重,将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形态。
首先,互联网可以通过自动化,大大强化自“函授”以来远程教育的一大特色,即教育内容的批量复制。“远端”不光能够获得一模一样的文字信息,还可以获得一模一样的视听信息,甚至习题、答疑乃至阅卷都可以自动化地批量完成。中国那些直播班还需要本地教师负责答疑,并熬夜阅卷,这些工作将来完全可以预期被计算机取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扩充的数据库,来应对学生们幼稚的提问。
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吗?芬伯格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实质上加剧了工业时代以来教育的机械化趋势,学生越来越像是工厂流水线中的“产品”,被批量订造出来。
就批量生产的产品而言,它们也许是越来越“平等”了,但这种作为机械产品的平均化并不是我们理想中作为“人”的平等。人的平等不是作为最终产品的平均化,而是说,每个人都应获得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通过敉平个性而获得的平均化并不值得欣喜。
而中国这些直播班所追求的似乎就是这种机械化的平等——尽可能减少考试分数的差距——这种理想即便可以做到,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穷地区培养出更多的考试机器,社会就会更和谐吗?如果“考试机器”本身是坏事,那么让贫穷地区出现更多坏事,岂不是更糟糕?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高中时暂时变成考试机器,到大学再全面发展也不迟啊,至少他们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不是吗?但问题是,如果这种新的教育文化继续扩张,大学的教育难道不也要随之改革的吗?落后大学不也该引入“那块屏幕”去复制先进大学的课程吗?当这种全面“复制”的教育方式扩张到所有领域,教育的均一化难道不是大势所趋吗?
关键在于,教育的意义仅仅被看作谋求某一特定目的的必要手段,例如中学教育是为了高考,大学教育是为了求职,如此一来,人们完全从功利的、效率的眼光来看待教育问题,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就被简单地理解为填鸭效率的差距问题。
但如果说教育不只是为了考试或求职,更是为了培育健全的、丰富的、自由的人格,那么,对于远程教育的优势就应当重新审视了。
芬伯格以“城市”与“工厂”对立,与其说学校像一所工厂,不如说更应该像一座城市,工厂出产的是产品,而城市诞生的是“公民”。在学校中,“照本宣科”地传授刻板知识只是教育的一个侧面。所谓“教育”远远不止发生在客观知识的复制方面,更发生于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学生主动地参与交流,是教育中更重要的环节,这也正是传统的学校教育始终难以被函授或自学取代的原因。
“那块屏幕”还需要弹幕
而在这方面,互联网也蕴含着新的机会,因为它在促进机械复制的同时,也可能促进交流和对话。芬伯格本人就大力提倡开发以“互动文本”为中心的在线教育环境。但他也注意到,要发扬这一进路并不容易——“以互动文本为基础的应用缺乏视频替代形式的生动,不能保证实现自动化,而且它们也不能包装和销售。“(《技术批判理论》中译本163页)
简单来说,这种开发思路是效率低下的。显然,如果把同一个视频同时直播给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再加入师生互动是极度困难的,更不用说家长和课外活动营造的各种交流活动,更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一提到的,成都七中的家长会帮助学生争取和诺奖获得者的对话机会,学生有拳击、游泳等丰富的课外活动。在这些方面,单靠“那块屏幕”是改变不了的。
但互联网并非没有改变这一切的潜能。就师生交流而言,直播平台中主播与“水友”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方式,主播通过“弹幕”实时接受天南地北的网友们的反馈,“水友”不只是被动的观众,而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就学生交流而言,各种互联网的同好圈也开辟了新的空间,传统上只能通过现场的户外活动(如踢球、跳皮筋)才能建立起的同学友谊,现在已经开始转向以打电子游戏为中心,而打电子游戏这件事情,又更容易通过互联网而跨越地域差距。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许多直播课程在支持弹幕的视频网站上播出,但效果并不总是很好,很多人发言并不是为了与他人交流,而只是发泄和喷人。而一些主播发起互动的目的主要也只是为了讨打赏。这样一来,弹幕在课程直播中发挥的功能就略显浮躁了。但我们应当意识到,无论哪条进路,教育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我们从工厂模式转变为城市模式,就立即可以获得成功。“工厂”模式有机械化的危险,而“城市”模式也有过度商业化或浮躁化的危险。对于新教育模式的探索还需要做很多努力,光靠商业公司的参与是不够的,更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等这些传统的教育者的广泛参与。
因此,传统教育者应当打破成见,不再将视野聚焦于互联网的自动化和机械复制的面相。而是要更重视挖掘互联网的交流维度。刷弹幕、打网游——恰恰是这两项在传统教育者看来不务正业的娱乐活动,有可能开辟出在线教育的第二条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