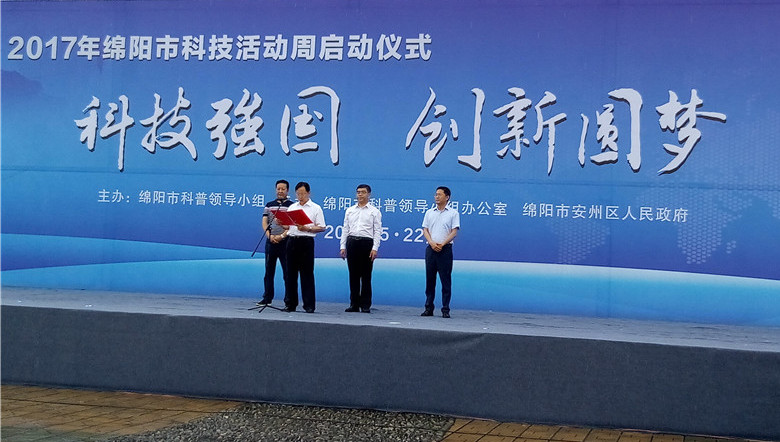最近的氛围让我有点惊弓之鸟,继续用上加密模式。这篇文章其实不值得加密,过两天我可能会默默解密。
最近有教师因为关于四大发明的言论而遭到处分,实在是令人震撼。我不想在这里重审对举报文化的警惕,只想聊聊学术问题。
这次事件比以往更加可怕的是,导致处分的言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学术问题。为此官媒都看不下去了,提出让“四大发明”争议回归学术。
什么叫学术呢?无非是讲道理、讲证据。学术问题不是简单的站队问题。学术研究也有立场,但并不是简单地拥护还是不拥护某句口号的问题,而是体现于论据选择和论证方式。如果没有论据也没有论证,只谈一句孤零零的口号,那是什么意义都没有的。
其实政治口号也有语境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共产主义好”,对不对?但如果某个人要求今天就立刻实现共产主义,取消私有制,消灭财产,废除货币,甚至瓦解国家和政党(按马克思的理想,共产主义实现后是不再需要国家这一暴力机器的),那么,他对不对?如果你要说他的想法不对,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共产主义坏”?
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只有某一种绝对固定的意思,只有一种非黑即白的结论。共产主义作为理想是好的,而作为现实政策是坏的;一国两制针对香港是好的,但在海淀区也搞一国两制就未必好了。学术的态度,或者说论理的态度,首先是不能简单化地、情绪化地、口号化地进行判断。
“四大发明是不是创新?”这一问题也是类似的,关键在于,我们正在谈论的“创新”是什么意思?那位老师用一整门课程讨论了创新的意义,然后根据业已建立的语境再来判断四大发明不是创新。他的观点当然是可质疑、可批判的,但也要从相应的语境下发起争议,而不是简单地从只言片语中就对此定性。
甚至网上的很多争论,都不再关心“创新”的概念问题,而是把问题转换成“四大发明好不好”的问题了。
事实上,我在一些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气质的科学史论述中,都没有看到说四大发明是“创新”的。人们一般是说,四大发明很伟大,很重要,是对世界人民的巨大贡献等等。
万里长城伟大不伟大?厉害不厉害?但它是创新吗?汉武帝破匈奴伟大不伟大?厉害不厉害?但这是创新吗?难道凡是好东西,就是创新,凡是不属于创新的,就不是好事?
“创新”一词早已用烂了,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最宽泛的意思来理解它,比如说,“创造新事物”就算创新。但如此一来,说四大发明是创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在自家门口挖个坑,那也算创新,我挖坑之前这里没有坑,这坑可是前无古人的新坑,我为世界人民贡献了一个崭新的坑,这算创新吗?
那些根本不深究概念的意义,不讲道理地把理论性的主张口号化、肤浅化的人,才是在无可转圜地自我贬低,他们把中国贬得什么都不剩,只剩下一些毫无内涵的标签——我们最伟大!我们最光荣!我们最厉害!除此以外,我们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他们就语焉不详了。
“创新”其实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在学术界有其独特的定位,有许多定义的方式。一些主流的定义其实是把“创新”看作一个经济学概念,意味着从科学、技术、到工业、商业的某种系统性的整合,并不是简单地“挖一个前所未有的坑”就算创新,而是必须产生经济效益才谈得上。
当然,即便从经济学上看,四大发明究竟是不是创新呢?倒也可以商榷,比如我感觉造纸术也许有一点点可以沾边的,印刷术发展史中也可能有类似的创新活动发生过(但决定性的并不是毕昇)。但这些就是比较具体的争议了,而大多数参与争论的人,甚至都没有多去思考一下“创新”这一概念的学术意义。
在十几年前,我经常能看到金吾伦等科哲界的老前辈谈论“创新”的意涵,但现在我们似乎越来越强调创新了,但对概念的辨析反而越来越陌生。
在最近的两次讲座中,我都列出了西方历史中最最著名的一系列“发明家”,包括:谷登堡(印刷机)、瓦特(蒸汽机)、富尔顿(蒸汽船)、史蒂芬森(火车)、摩尔斯(电报)、惠特尼(可更换零件)、达盖尔(照相术)、爱迪生(电灯)、马可尼(无线电)、贝尔(电话)、诺贝尔(炸药)、莱特兄弟(飞机)、福特(汽车/流水线)。
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有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都不是第一个创造出括号中那种东西的人物,同时,他们又都是最成功地对括号中的事物进行商业化开发的人物。
但这些人并非浪得虚名,他们的名声并不是出于误会,而是依据西方人对发明和创新的理解,他们确实是技术史中的关键先生。
当然,我们可以反对西方人的概念,搞出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以自己的眼光对历史人物做重新评价。但问题是,我们先得对现代世界主流常识有所认知,才谈得上超越他们。而不是像井底之蛙那样,对外界的观点压根都没听说,讨论的问题完全脱节。比较一下在维基百科上innovation词条和国内对创新的谈论,就会对这种大众知识的脱节深有感触。
我最近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古代非但没有“科学”,甚至连所谓“技术”也没有。当然,我并不是依据“技术”的日常理解,即各种实用器具和生产工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哪个文明没有技术,从人猿揖别开始人就与技术互相构成。但是,如果以西方现代的“techn-ology”概念来看,中国古代确实缺乏某种作为“逻各斯”的技术。中国古代的这种匮乏,与“科学”的匮乏是共通的。
具体的讨论就暂时不深入了。倒是我最近讲座中用到的一个新比喻值得再记一下:
问“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类时,鉴于“科学”之一概念的根源在西方,我们实际上问的是:在中国古代是否能找到由西方人所定义的“科学”的部分内容?比如,西方科学中有天文观测,中国商朝就有;西方科学中有小孔成像,墨经里就有;西方科学里有勾股定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
与之类似地,我们可以换一种问法,比如说,“西方古代有无儒学”?那么我们可以依据中国传统来界定儒学的内容。比如说,儒学中有对孝顺父母的强调,西方人圣经里头十诫中也有;儒学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有类似的讲法;儒学里有讲格物致知,西方当然也有;儒学传统里有讲天人感应,西方也有讲大宇宙小宇宙对应的;儒学里有心学的分支,西方也有唯心论的分支,等等……
如此一来,我们是不是也能说,西方古代也有儒学?甚至是不是可以说,在许多具体内容上,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早?
真要这么讲,也不是讲不通。但是我们会觉得有哪里不太对。西方古代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儒学,但又在何种意义上不能说有儒学呢?很简单,如果我们把“儒学”当作一个整体性、连续性的“传统”,横向来说,儒学的各种具体观念之间有某种整体的统一性,纵向来讲,儒学从先秦到宋明有连续的发展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才称之为儒学。而如果我们拆散了儒学的整体性,把儒学看作一条一条各不相关的具体内容的集合,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在其它文明中也找到其中若干条内容的对应物。
“科学”也好“技术”也好,如果对照于“儒学”来论,那也是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拆散它们,看一个个具体的科学成果和技术产品,自然能够在其它文明中找到对应物。但如果我们更多地考虑它们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那问题就不同了。
关键在于,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找寻或确认伦理或科学的跨文明的普适性?是为了寻找某种历史发展的趋同性?还是为了比较不同文明的差异?或是单纯为了寻找民族优越感?
如果弄不清为什么提问,也搞不清讨论的语境,只是拼命强调“中国古代有科学”之类,和强调“西方古代有儒学”类似,其实是完全不知所云的事情。